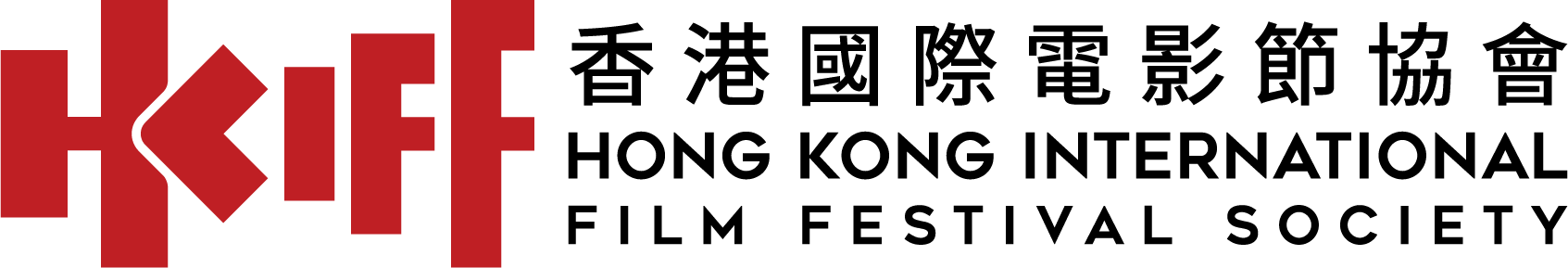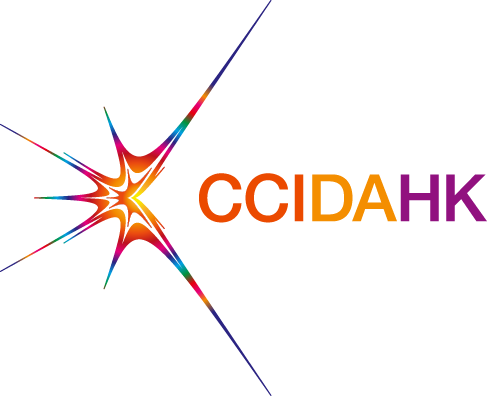2017
早逝天才-尚維果全展
尚維果(1905-1934)活在世上短短二十九年,只完成了三部短片及一部長片,已足以在影史留名。他不只拍出傳世經典,更影響深遠,既是法國詩意寫實主義的先驅,亦為後來的法國電影新浪潮立下典範。《操行零分》(19 3 3)借一所學校,呈現建制的虛偽醜陋與強權高壓,孩子們則敢於反抗。結果一度被禁,卻成為日後杜魯福拍《四百擊》(1 9 59)的靈感泉源,更直接影響英國新浪潮悍將林賽安德遜創作《假如…》(1968)。
尚維果的父母都是無政府主義者,父親在獄中「被自殺」,他被送進寄宿學校,反叛基因就在他日後的電影裏起革命。19 29年他在巴黎遇上攝影師鮑里斯考夫曼(蘇聯導演維爾托夫的弟弟),兩人開始緊密合作。短片《尼斯印象》(1 9 30)已可見維爾托夫「電影眼」理論的影響,捕捉人眼忽略的真實。尚維果更受布紐爾的《一條安德魯犬》(19 2 9)啟發,在作品注入超現實色彩。
《阿特蘭大號》(1 9 34)公映時,尚維果已病重。電影因片商認為不夠商業,被大幅刪剪,片名及音樂都改了,及後才獲逐步修復及重新肯定,並多次入選影史十大,高達和貝托魯奇都曾在自己的電影裏向它致敬。高蒙電影公司幾經考證,於1990年完成了主要修復,2001年再作修訂。到今年,最接近影片原貌的修復版本於博洛尼亞影展曝光。同時發現一直藏於米蘭電影資料館的《操行零分》拷貝,比大家熟知的版本更完整。事隔八十多年,大家終可一睹它們的本來面目了。
誰為歷史下定論?
「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」,這句虛無主義者津津樂道的名言,來自二戰納粹軍官派普(JoachimPeiper)。的確,許多官方的歷史紀錄和當代詮釋,經過篩選與剪裁,掩飾與歪曲,令歷史化為碎片,真相消失於塵埃。於是,慰安婦只是「有執照賣淫體制下的工作者」;二二八事件源於「日帝遺毒與共黨煽動」;光州民主化運動變為「親共主義者主導的內亂陰謀事件」。
上述名言其實還有下句:「事實真相只有親歷者才知道」。歷史或許可以篡改,但集體記憶難以模糊。個人經歷與其所處身的時代變遷互相交纏,透過每個人的生命故事,以及時代動盪後的反身凝視,能對照歷史的主流敘述,反思歷史的真實面貌。電影,成為了歷史的使者,再造我們的世界觀,讓大眾對過去的記憶與官方的主旋律抗衡,還民間一把聲音,還歷史一個公道。
歌德學院特別邀請香港及中、台、韓、日等地與德國的電影學者,共同策劃「誰為歷史下定論?」專題,探索電影中所呈現的大眾歷史。選映的影片呈現不同政權之下,人民生活受到政治外力影響的故事:《玄海灘為證》(1961)裏韓國少年兵為日本殖民國打仗、《儀式》(1971)裏日本少年受困於帝國主義的父權體制、《香蕉天堂》(1989)裏台灣外省兵在白色恐怖下委曲求全、《霸王別姬》(1993)裏中國名伶在時代洪流歷盡滄桑以及《千言萬語》(1999)裏香港癡男怨女為社會公義抗爭。平凡的故事,展現了歷史裏不凡的人性。
歷史雖然論述過去,但絕非過去,而是隨時代更迭重生。光影,超越時代的黑暗,保存人民的記憶,讓我們直面歷史,迎向未來。
合辦

永遠的女優—原節子(二)
原節子(1920-2015)離世後,我們去年曾辦過一次小型回顧展。匆匆寒暑,念念不忘,今回再續未了緣。
日本人眼中的絕世美人,原節子之美,並非不吃人間煙火;相反,正是她「因為懂得,所以慈悲」的洞悉世情與善解人意,總能撫慰心靈,宛如端坐蓮台。定格於小津安二郎的光環下,《晚春》(1949)裏侍父至孝的女兒;《東京物語》(1953)裏體貼翁姑的兒媳;《秋日和》(1960)裏忠貞堅忍的母親,使她成為國民心中完美女性的象徵。「婉約中不失剛愎,謙順裏不減風華,在五十年代我們成長的黑白歲月,那是紙窗上一枝顫抖的梅影。」(董橋)
小津說,原節子是「用細微的動作自然表演強烈的喜怒哀樂的類型……這樣的表演能夠輕鬆展現細膩的感情」。的確,她樸實無華的演技,在與黑澤明、木下惠介、今井正等導演的合作中,展現了不一樣的風采。在《安城家的舞會》(1947)中演繹剛強、獨立、自主的女性,擺脫封建的桎梏;在《驟雨》(1956)、《娘.妻.母》(1960)中,微妙呈現妻子角色的內心矛盾與覺醒,在成瀨巳喜男的鏡頭下流露多姿的神韻。
原節子拍畢稻垣浩的《忠臣藏》(1962),43歲後絕跡影壇,回復本名會田昌江,神隱於小津鍾情的鎌倉直至離世,終身未婚。她說過自己從未以拍戲為樂,以後毋庸再做不喜歡的事情。或許,在光影夢幻裏歷遍悲喜,訴斷衷腸,早已領悟過盡千帆皆不是。唯有電影,保存了她時而淺笑、時而低泣的身影,讓她的美麗如一剪梅,永恆傲放於天上人間。
征服電影!
征服電影,或被電影征服!
人心要征服的,最終並不止於電影。
二十世紀二、三十年代的德意志,一方面享受初生電影工業的精神洗禮,另一方面則抵受兩次大戰之間經濟蕭條的煎熬。生活顛簸催生意識撕裂,對於種種切身社會問題、民族整體去向,基於不同出發點,竟產生截然不同的結論,並且彼此對立,衝突勢所難免。蘇維埃社會主義革命成功,一石激起千重浪,整個歐洲都沸騰起來。浪漫的集體情緒極度高漲,鮮有不感染者,分別只是向左傾還是右傾。前者擁抱馬克思主義,後者則投向法西斯的懷抱。
假如電影真是布爾喬亞欺騙人民最強大的工具,無產階級必須把它奪回來,建設紅色夢工場,那麼,德國左翼電影人掛出以「征服電影!」為口號的標語,自是順理成章。布萊希特、艾斯拿、斯拉丹杜多夫、皮爾祖西……一眾劃時代的歷史才人,深信革命不是請客吃飯,電影正是深耕細作的場域,乃群策群力,致力與紀錄片真實影像相輝映的寫實主義實踐,承襲蘇聯蒙太奇理論的影像經營策略,拍出了《克勞澤大娘升天記》、《天下誰屬》等傑作。可惜好景不常,人民始終選擇了國家社會主義,右翼政府取締革命電影,底片被摧毀,演員流亡。納粹電影君臨天下,只是他們要拍的竟也是納粹版的《波特金號戰艦》,《希特拉青年團》應運而生;意識形態相反,美學形式卻如出一轍。
畢竟,光影如此多驕,引無數英雄競折腰!說到底,不論左右,爭相去征服電影的同時,到底難免發覺,在歷史的長河中,其實是他們自己被電影征服了。
合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