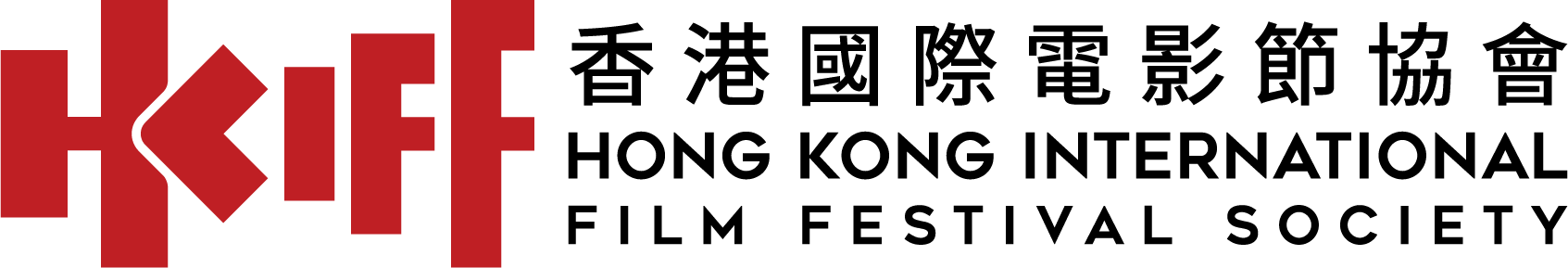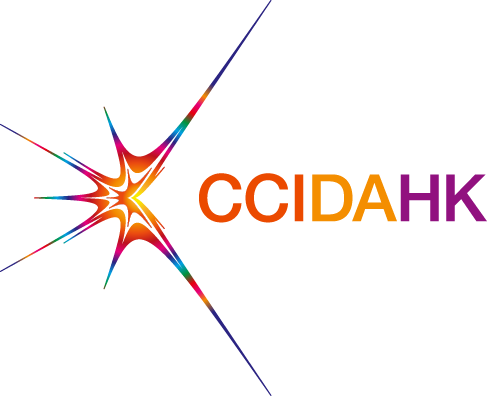2024
寒梅傲立 — 瑪特美莎洛斯的電影日記
「女人想拍電影是一個笑話。」瑪特美莎洛斯談及當年遭受的尖酸嘲諷與困阻,一笑置之。屹立影壇逾半世紀,創造無數傳奇─ 匈牙利第一位執導的女性,首位榮獲柏林金熊獎的女導演─ 與其前夫電影大師楊素的成就並駕齊驅,風格卻傲然自立。
拍紀錄片出身,美莎洛斯的攝影機張弛有度而極富實感,擅於探討女性的存在窘境。刻劃為女、為妻、為母的多重身份,將工廠與窩居的平凡空間, 塑造成個人與家庭及社會的角力場,揭示女性置身父權操控與道德規範下的拉扯碰撞。從未婚生子、非婚領養、借腹生育等禁忌題材,到實時直拍生產過程,模糊虛構與寫實的界線,盡現美莎洛斯的藝高膽大,凌駕時代。
猶如稚子看世界,美莎洛斯觸覺敏銳,鏡頭簡約純粹而極具穿透力,與女性複雜多變的心理狀態層層互扣。或寂寞、或忐忑、或恐懼、或放肆, 真情實感不作矯飾, 冷靜目光不帶批判,卻不乏體諒;充滿張力的特寫與凝鏡,總未忘捕捉每張臉上的一點倔強與柔韌。雖被譽為女性主義電影的先驅,美莎洛斯卻從不以此自居:「我只是在拍關於人的電影。」
從個人自強、女性團結到歷史反思,在不同時期的作品裏,於瑪麗亞維拉迪、伊莎貝雨蓓、莉莉莫羅利以至蘇莎仙歌絲等主角身上,不難發現美莎洛斯的自我身影。由父母被迫害亡故而變為孤兒、被領養到成為出色導演,她的人生體現了女性在性別及藝術解放的層層蛻變,亦折射着東歐近一世紀政治及社會的風雲變遷。在其最著名的「日記三部曲」,透過記憶結合夢幻與真實,將個人成長傷痕縫入家國歷史滄桑,召喚回憶的幽靈,超度民族的苦難。
如今九十有二,笑到最後,是堅守信念的自由靈魂。
故調新彈 — 大師的自我對照
重拍舊片的歷史源遠流長, 不少人只視之為創作人的江郎才盡。不過, 由大師級導演親身重拍自己的舊作,意義卻大有不同;把自己作品提煉至登峰造極,大抵是每位導演重拍舊作的心願。
跟同一素材再續前緣, 箇中原因不一而足: 有默片變為聲片, 有黑白變為彩色, 有標準變為闊銀幕。當中代表着電影製作技術不斷革新, 同時亦反映着時代變遷─小津安二郎電影裏的孩子淘氣依然, 卻瞥見日本從戰前蕭條過度至戰後復興; 阿培爾岡斯更以電影控訴歷史重蹈覆轍, 以迥異手法將反戰主題一再昇華至全新境界。朱里安杜維威將曲終人散的法式感性哀愁變成美式浪漫悲情, 既對照兩地文化之不同, 亦反映他因戰禍避走荷里活的心態轉變。
時代進步,社會開放,審查尺度隨之放寬,亦令曾被迫刪剪的作品,終可以導演理想的版本問世。稻垣浩在《手車伕之戀》補遺無法松想向寡婦表白的精彩一幕;而在六十年代重拍的《雙姝怨》, 威廉韋勒亦可忠於原著劇場版本,同性愛的暗示已毋須避諱。不過話說回頭,審查利刃下那種含蓄暗喻與弦外之音,又自有一番韻味。
力臻完美固然深入大師骨髓, 但故調重彈未必純為自我修正, 或許更是一箭雙雕。希治閣曾對杜魯福說, 1 9 3 4年的《擒凶記》是業餘水準, 1 9 5 6 年重拍版才是專業之作。貴為緊張大師,這句話該只是「麥加芬」,潛台詞是前作拙樸,後作雕琢,各擅勝場。希翁才氣橫溢,魯爾窩路殊亦毫不遜色, 一揮魔術棒將黑色犯罪片《夜困摩天嶺》變為西部片《虎盜蠻花》;同一故事,兩種類型,堪富利保加與祖麥基利,誰也搶不了誰的風頭。
李奧麥加利41歲時拍成《瓊樓密約》, 其後經歷歲月洗禮與車禍險死還生, 對人生、愛情以至命運自有一番不同感悟, 到59歲時重拍成《金玉盟》, 臻至爐火純青。無論如何,不管舊瓶新酒或新瓶舊酒,清樸與醇厚各有所好;若一併品味對照,大可嚐出層次不同的嶄新味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