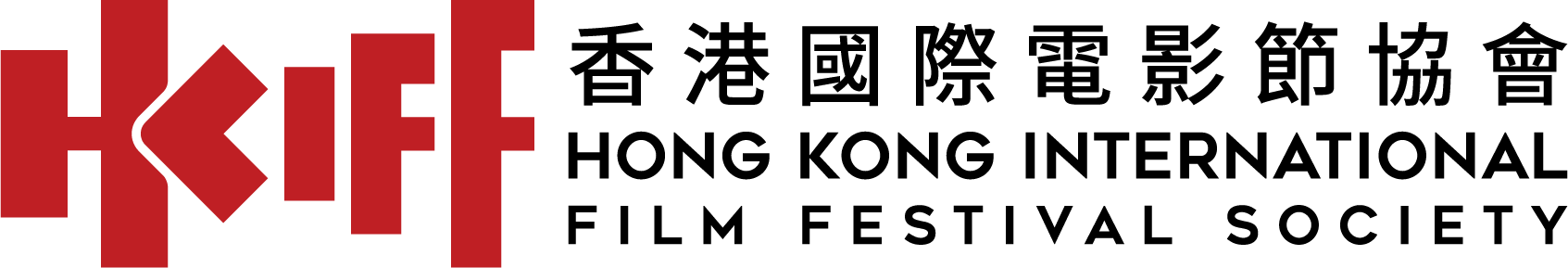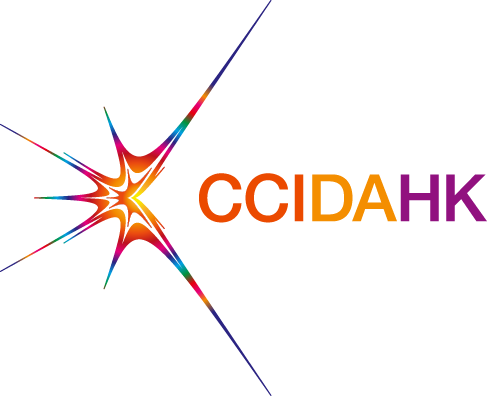2018
瘋狂的睿智— 華納荷索
「當我們記得大家都是瘋子時,所有的謎都會消失,生命也會得到解答。」 最懂馬克吐溫此言深意,莫過於華納荷索。療養院侏儒肆虐狂歡、野人被教化後中槍身亡、卑微小兵殺妻自盡,荷索的電影裏,盡是畸零怪誕的人和事。瘋狂影像,召喚靈魂的甦醒,毋須像醫生將卡斯伯侯沙的腦袋解剖研究,電影早已揭示生命真相。
「我就是我的電影」荷索如是說。超越理性、批判文明,闖進極地絕境,做自己的夢,也說別人的夢。對電影奉如宗教虔誠,偏執於創新電影語言,以實景實事結合詩意想像,臻至「令人狂喜著迷的真實」。這種神秘得近乎神聖的迷思,建構靈視大師的祭壇,創造不朽的電影神話。
認定拍電影是天命,自學所有電影知識,幹苦工賺錢成立製作公司。鋼鐵廠打工煉成無堅不摧的意志,為拍戲不惜冒險犯難:拍攝《生命的訊息》(1968)時,拔槍威脅希臘駐軍殺警自轟;拍《新創世紀》(1971)在喀麥隆被捕入獄遭毒打兼染頑疾;製作《天譴》(1972)在亞馬遜叢林困於急流暴雨險死還生。將現實的災難折磨融入電影,成了真實而震撼的情感力量。
或說擇善固執,或說冥頑不靈,荷索電影捕捉的,既是不容於社會的人物,亦有自我投射的身影。狂傲天才不愁寂寞,與識於微時的「極端自我主義者」寇斯金斯基相生相剋,雙槍互指太陽穴,逼到彼此精神崩潰,卻達極致的創意巔峰,《胡錫傳》(1979)、《陸上行舟》(1982)等合作的五部電影公認為史上經典。
今期選映的九部荷索早期作品(加一部金斯基紀錄片),奠定其特立獨行風格。第四十二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及下期Cine Fan節目,將繼續深入其異類國度。
合辦

安東尼奧尼— 建天地 見人間
眾裏尋他,萬古惆悵,心事還將與?銀幕上的她,憑窗對鏡,輕巧轉身,說了一兩句溫柔的話。我們都認出那股荒涼孤獨,敘事在觀眾預期的地方中止,懸空了。有甚麼稍稍離開,心動了幾回⋯⋯正是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(1912-2 0 0 7)的聲畫組合;他讓我們認識到,電影語言竟可如此細密,活動影像怎麼樣都有可能。
三十八年前,法國思想巨擘羅蘭巴特向安東尼奧尼致送了一封公開信,高度贊揚了安氏作品,並枚舉了其為藝術家典範的三大特徵:對歷史、對人文時刻保持關注和警惕;擁有洞悉人性和分辨世情真偽的智慧,以及最弔詭的—身處時代變局中,不惜時刻受威權威脅的脆弱性。
十年前,安東尼奧尼在羅馬家中逝世;生命和藝術俱脆弱,只宜小心輕放。其逾六十年的創作生涯留下了十六齣長片(其中一部是紀錄片),部部佳構精品。十年後的今日,在堅持變得可笑,不義彷彿牢不可破的當下,回到安東尼奧尼的電影世界裏,尋求那易碎的絕對,簡直是奢侈的必須。
無論是直探感性禁區(《迷情》、《夜》、《情隔萬重山》)、批判資本主義無形壓逼、叩問生產異化下的生活意義(《赤色沙漠》、《春光乍洩》、《無限春光在險峯》),抑或於人性窄縫中探究存在出路(《過客》、《女人女人》),安東尼奧尼均顯得全神貫注,珍惜經營。所有演出,在其靈活運動的影機收攝下,滙成超越道德、出入情色無礙的人和事。說他漂亮他是進取,說他左翼他便是美。
延伸閱讀:
張偉雄-現實、絕對和神秘的春光, 刊於《定義現代 安東尼奧尼》(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,2009)
黃愛玲-六十年代與安東尼奧尼, 刊於《定義現代 安東尼奧尼》(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,2009)
羅卡-不倦探索的先知, 刊於《定義現代 安東尼奧尼》(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,2009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