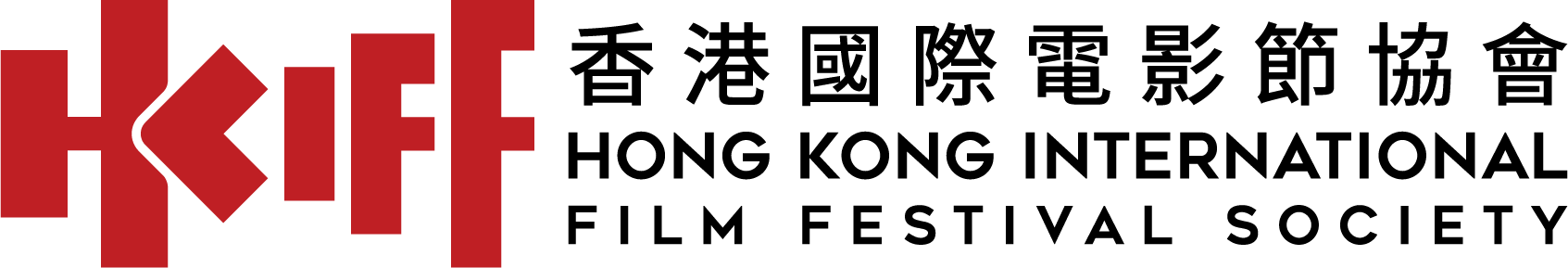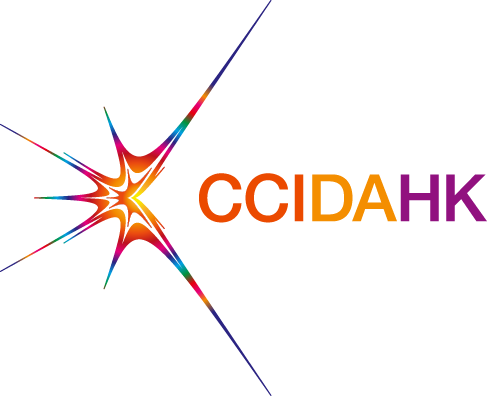2019
禁不住的荒謬:中歐與東歐的荒誕電影
三十年前,東歐變天,「歷史終結」,資本主義號稱全面勝利。可是人們很快發現,老大哥沒有離開,走了法西斯,來了共產黨,再換上資本魔。宰制依然慘烈,如果真有不同,倒是以前還算容易覺察發現,走資卻無孔不入,在不知不覺間,更多的罪惡假市場之名施布。
曾幾何時,人生的荒謬在極權政治下一覽無遺。一覺醒來,發覺自己變了一隻大甲蟲;又或者進餐之際,警察破門而入,被捕者不須曉得犯了何罪,便隨時被送上絞刑台……一切卡夫卡式處境,除了彰顯人生徒勞,也突出了在種種宰控下,抗爭儘管無功,卻是必須。
卡繆說,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,就是自殺。世事愈荒謬絕倫,人愈必須堅持活下去。也是這個緣故,啟迪觀眾在虛無中尋找意義的荒誕電影,於「蘇東波」之前,一度百花齊放,在捷克新浪潮、蘇聯諷喻電影、波蘭和羅馬尼亞新電影的波濤裏,都找到它們蹤影。
無論是蘇聯叛逆女導姬娜穆拉托娃,還是捷克的帕維祖拉錫、彼得蘇蘭或楊史雲梅耶,又或者是羅馬尼亞的路西安賓提利,以至波蘭怪傑波蘭斯基與動畫大師聶辛斯基,他們均曾努力嘗試,以巧妙的諷喻手法,加入超現實和實驗元素,透闢他們身處的荒謬現實,直探人類存在的深層意義。不少荒誕電影的傑作,大多遭逢禁映的命運,卻阻擋不了歷史的肯定;待完成二、三十年後,終獲世人廣泛認識,也讓時代的真相,在光影裏重現。
對,人生是荒謬的,但幸好我們還有電影。
客席策劃:加比奧佩列茲
加比奧佩列茲在南加州大學主修電影研究並副修電影製作,取得首個博士榮銜。其後從捷克到埃塞俄比亞教授電影,更從科索沃到香港等地策劃電影系列。現正編寫奧遜威爾斯專書。
虛無之愛 幽玄之美—川端康成文學映畫
如夢幻泡影,如露亦如電。塵世一切的美,幻化無常,剎那消逝;人間一切的情,虛渺徒勞,終將凐滅。「方生方死,方死方生」,川端康成(1 8 9 9 -1972)將美麗與哀愁,冰封於晶瑩剔透的字裏人間,凝住一瞬永恆,達致空靈的藝術至境。
「以敏銳觸覺、高超事技巧,表現了日本人的精神特質。」諾貝爾文學獎給川端的稱譽,概括了其文學的獨特風格。滲透大和「物哀」之美,提煉出一種生命質感:看《多謝先生》的峰巒起伏,感悟人生飄泊;聽《美麗與哀傷》的除夕鐘聲,達致觸景傷情、物我和融的美學。《山之音》的空山迴響,《雪國》的白雪茫茫,從自然萬物稍縱即逝的極美,川端掌握「生命閃光」,在輕盈似羽的故事裏,超越死生,昇華為靈性的體現。
濃厚日本古風之上,川端文學融入西方文化思潮,摒棄世俗道德的覊絆,情思無盡。文章翩翩化實為虛,與光影幻像契合,成為導演的靈感泉源─由殿堂大師五所平之助、清水宏、成瀨巳喜男、吉村公三郎,以至新浪潮旗手篠田正浩、增村保造、吉田喜重,將詞藻的瑰麗化為畫面的豐盛。岡田茉莉子在《女人之湖》(1966)的冷豔、岩下志麻在《古都》(1963)的秀雅、岸惠子在《雪國》(1957)的風情,一代女優活現川端的「女性讚歌」,以超塵脫俗姿容,蕩漾貪嗔情癡;透過《伊豆舞孃》(1933)裏田中絹代的淚,以至《千羽鶴》(1969)裏若尾文子的死,淨化虛惘心靈,臻達美之極致。
沒留隻字,川端結束生命,完成一生追求的耽美。「無言的死,就是無限的活」,在文字與光影的不朽裏,涅槃重生。
鳴謝日本國家電影資料館借出
《伊豆舞孃》、《多謝先生》、《千羽鶴》(1953)、《美麗與哀傷》、《女人之湖》及《千羽鶴》(1969)之35 米厘拷貝。
鳴謝日本文化中心借出《雪國》之35 米厘及《古都》之16 米厘拷貝。